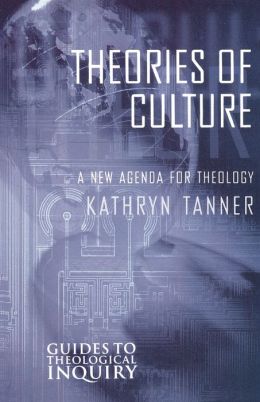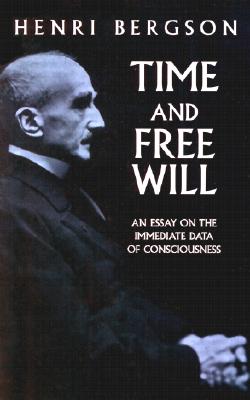
伯格森(1859-1941)是十九至二十世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作者透过这本书,尝试解决“自由意志”这个问题,并尤其对康德的自由意志之观念进行批判。这本书共分为4章:透过第一及第二章关于绵延(duration)与广度(extensity)、陆续发生(succession)与同时发生(simultaneity)、质量(quality)与数量(quantity)的讨论,并在第三章来解决自由意志的问题。
第一章:心理状态的强度
作者在这一章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心理状态是否有数量上的差异?当我们说这一个数目大于另一个数目,并由小至大排列时,这是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数目是在什么意义上大于另一个数目。但对于心理状态的强度而言,它本身既是不占空间的,为何我们可以把心理状态的强度赋予数量来看待呢?
作者认为,当我们谈及数量时,它必然是涉及“空间性”,因为唯有在空间里,我们才能够把东西“固体化”并“分隔”,如此,数量才能够产生。因此,当我们把心理状态的强度等同于数量上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正把不占空间的转化为空间性的东西。而其实,不占空间的状态,如心理状态的强度,是质量上的差异,而非数量上。
作者分析了许多心理状态,而其中一个例子是道德的情绪:怜悯。我们经历这情感的起先,是设想自己处于被怜悯者的角度,从而感受其痛苦。但如果这情感的内容只限于此,则这情感将使我们设法避开不幸的人们而不去帮助他们,因为苦痛对于我们自然是可憎可怕的。憎恶情感确实可以是怜悯情感的根源。然而,因着对未来灾祸无法预知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恐惧感,使我们对不幸的人产生同情。真正的怜悯,其内容不大是害怕受苦,而是愿意为着他人的不幸而受苦。受苦的愿望是微弱的,我们几乎不希望它变为事实,但是我们逆着自己的意志而仍然怀着这个愿望。所以怜悯的要素在于我们要求自卑与企望痛苦,并使我们暂时对我们种种肉体上的好处不加以考虑。在这里,作者强调了,怜悯的强度,并不是数量上的,并非只涉及单一状态的数量上差异。怜悯在强度上的增长,是一种在性质上的进展:从厌恶进入恐惧,从恐惧进入同情,从同情再进入谦卑。
由此,作者透过第一章总结说,强度这一观念具有两个面向:1)代表外因(represent
an external cause)的表象性意识状态;2)不代表外因而自足的情绪性意识状态。对于表象性意识状态,其对于强度的知觉就是对于原因大小的估计;而对于情绪性意识状态,我们猜测在此状态中所涉及的简单内心现象(simple
psychic phenomena),而把这些现象的多少称为强度。
因此,强度这一观念涉及两个面向;其一,从外界带来广度上大小这个观念;另一,从意识深处带来内在众多性这个影象(the
image of an inner multiplicity)。
内在众多性是什么?作者因而进入了第二章关于意识状态的众多性的讨论,并阐述了绵延这一观念。
第二章:意识状态的众多性 –;关于绵延的观念
伯格森认为,众多体可分为两种:1)数量众多性(quantitative
multiplicity),用于物质的东西,它们可在空间被数出来;2)性质众多性(qualitative
multiplicity),用于意识状态,除非被象征地被置放于空间里,否则无法被数出来。
作者同样地用了许多例子来阐述“数量众多性”这一观念,而其中“羊群”的例子较容易理解。当我们看见一群羊,并说里面有50只羊时,虽然每一只羊都各自不同,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说有50只羊,乃是由于大家同意不去理会羊的个别差异,而只理会羊的共同点。因此,数量众多体是纯一(homogeneous)的。虽然如此,它们必须在某方式上彼此有别,我们才能够计算它们。我们能够计算并列举它们,乃是因为它们在空间所占的位置上不同,或是在空间上与其它羊只同时并列。因此,“数量众多体”是纯一及空间性的(quantitative
multiplicities are homogeneous and spatial)。 除此之外,由于数量众多性是纯一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符号(symbol),例如,一个总和:“50”。
“性质众多体”则与“数量众多体”相反,它是多样性(heterogeneous)并且是时间性的(temporal)。就如在以上提及的“怜悯”这一情感,其中过程其实正经历着许多不同的情感,而这是性质上的差异,而非同质。同时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些情感并列出来,或后来的情感否定了之前的情感。在绵延这一观念里,这些情感是互相延续、互相渗透的。因此,“性质众多体”是多样性的(heterogeneous),连续并互相渗透(continuous
and interpenetrating),向前迈进的(progressive
or temporal, an irreversible flow, which is not given all at once)。由于“性质众多体”是多样性并互相渗透,因此我们无法赋予它任何符号;因此“性质众多体”是无法被表达的。
作者在本章要表达的是,绵延(duration)是“性质众多体”(qualitative
multiplicity),而它与时间(time)是不同的。当我们谈论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想着一个纯一的媒介;而在这媒介里,我们的意识被并排置列,如同在空间一样,以便构成一个能够被计算的无连续性的众多体。如以上我们在尝试分析“怜悯”这一情感时,我们把这“性质众多体”分化,并按照这些不同的情感被知觉的优先次序并排置列在时间里。因此,时间其实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正正是空间的概念,一个纯一的媒介。
绵延,是完全性质性的,它是种种性质的“陆续出现”;这些变化互相渗透,互相融化,没有清楚的轮廓,在彼此之间不倾向于发生外在关系,又跟数目丝毫无关:纯绵延只是纯粹的多样性。就如一首曲子,每一个音符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融化,以至整首曲子似乎成了一个“有机”的完整体,并对我们的情绪产生影响。倘若我们把这首曲子的每一个音符分隔开来,并给予某个音符过分的专注时,这首曲子就产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已不再像原本的曲子那样对我们产生影响。
因此作者总结道,意识状态有两个层面:1)表层的意识状态,一个被投射到空间的自我;与2)深层的意识状态(deep-seated
conscious states),一个在绵延下的自我。深层的意识状态,是跟数量不相干的,是纯粹的性质;它们混合到一个程度,以致我们无法知道到底它们是一个还是多个,以致我们甚至一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它们就不得不即刻改变它们的性质,就如曲子一样。
第三章: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作为人们的意志状态之一,同样的也是“性质众多体“(qualitative
multiplicity),绵延的。作者对自由意志的论述,主要是为了批判康德的自由意志之论述。康德把空间与时间混淆在一起,而此混合必然引致人类的行为是决定于因果律;为了解决此难题,康德因此认为自由意志是处在时间与空间之外之范畴。
因此,为了解决自由意志之问题,伯格森透过以上的论述,建议把时间与空间分开来,并认为意识状态是绵延的。在绵延里,并没有事件的并排置列(juxtaposition),因此也没有机械式的因果律(mechanistic
causality)可言。
最后,作者总结道:
“我们在生话中有时做出重要决定;这些时刻是独特无二的,永远不能再度出现,如同一个国家的过去历史永远不能重演一遍一样。我们应该首先明白:这些过去状态所以不能用文字充分地表达出来,或者所以不能通过简单状态的并排置列而被人工地重造出来,正是由于在其动力式的单一性上以及在其完全性质式的众多性上,它们是我们真正的、具体的绵延之阶段;而这种绵延是一种多样性的、活生生的东西。其衣,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动作出自一种心理状态,而这状态是独特无二的,永远不能再度出现的;我们的动作所以被宣称为自由的,正是由于这动作对于这状态的关系是无法以一条定律表示出来的。我们最后要明白:一来,必然决定关系这个观念自身在这里丝毫没有意义;二来,在一动作尚未完成之前,我们谈不上能否预知这一动作,而在一动作既已完成之后,我们也谈不上能否断定相反动作的可能性。”
自由这问题来自一种误解:把陆续出现(succession)与同时发生(simultaneity),把绵延(duration)与广度(extensity),把性质(quality)与数量(quantity),混淆在一起。